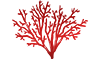陈澄不知道是因为她自己决定这么做,所以任务变成了这样,还是任务本来就这样,只是她恰好提前猜中了。她只感觉无比头疼,因为当个国会议员无法掌控行政权,她必然要当上总理。
而以她现在的年龄和资历,想当上总理,就必然要与魔鬼结盟,要组成联合政府,就会招致整个德共的敌视。她甚至能想到他们会以怎样的措辞在报纸上锐评她,无非是“狡猾的资本家”、“靠最肮脏的手段窃取人民的权力”之类的。
像是慷慨激昂的台尔曼会说的话。
离开德国时,陈澄听说他在汉堡码头组织工人罢工,声援英国罢工的工人。即使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使得英国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煤炭,而汉堡码头工人从中收益良多。
对德共的很多行为,陈澄都能键政吐槽一波,唯独对罢工,她不予置评。切实地讲,响应式罢工起不到太大作用,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传达一种反抗精神。在高失业率的重压下,汉堡这次罢工可能不会如愿涨薪降工时,连英国的罢工也不会成功。
感性上来说,英国工人或许会感激德国工人的声援,但声援带不来食物和储蓄,罢工会在缺衣少食下走向末路。如果趁机缓解下德国的失业率,让德国工人集资购买粮食送往英国,支援罢工,保障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最终可能能沉重打击英国境内的资本家。
当然,这是完全理想化的情况,是完全不考虑人的理想信念和心理情感、也不考虑两国外交风险和国际观瞻的方法。所以她只是想想,不会把这个想法跟任何人说,更别说去劝台尔曼这么做了。
毕竟,打击了英国的资本家,还有德国、法国等国的资本家。欧洲这块地方又小又破碎,就像个大号神罗,分裂才是主题,联合只是一时的意外。且不说苏联和共产国际能提供多大的助力,即使真能完成赤化欧洲的目标,放眼世界,还有美国在旁虎视眈眈,这种零零碎碎的罢工和打击实在是收效胜微。
不过,说不定他们想要的不是罢工的诉求,而是“罢工”本身,不是反抗后的幸福生活,而是“反抗”本身呢?
她关上光幕,打开房间里的灯,翻找近期的国际报纸,很快知道了那场罢工的结果:矿工们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降低工资10%,废除7小时工作制的条件。除了赢得国际无产阶级的尊敬和支持,引发社会震动,他们要争取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争取到。
对此,她只能回以一声叹息。
从这一角度来说,个人的力量在国家,甚至国际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能施加的影响有限,除非她身居高位,尤其是一个区域强国的政治高位。
她又一次打开光幕,盯着高级任务出神片刻,光速关掉它,躺回床上睡觉。
新一年到来后,返回德国的计划就被提上日程。
陈澄离开前把一切事务都交给戈培尔、夏莉和文特尔处理了,她估计三人组应该能撑几个月,至少在账户上的资金用完之前都不会出大问题,只是担心假释出狱的希特勒搞事。不过露伊莎和乔治不提,她也不好开口把劫后幸存的一家人再拆散,只好继续窝在佛罗里达的庄园里,陪露伊莎复健、玩游戏、听新闻电台。
年后这段时间里,美国媒体对英国佬异常上心,尤其是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热度非常高。
在不知道转了几手的电台媒体口中,丘吉尔声称自己粉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企图借罢工消灭带英,称霸世界的阴谋,宣称自己想赶走苏联驻英大使,完全结束英国跟苏联这种“貌似友好”的状态。为了反苏反共,他甚至跑去访问意大利,大捧墨索里尼臭脚,大赞法西斯主义好,听得陈澄七窍生烟。
“丘吉尔!丘吉尔!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他在夸法西斯?”
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试图平息怒气,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是的,他在夸赞法西斯意大利。”
“墨索里尼哪里好?是肆意侵犯公民权利好?还是对平民严刑逼供好?”
她想起去年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古语说“苛政猛于虎”,放在意大利,就是法西斯猛于黑手党。诚然黑手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作为政府,肯定不该不明辨是非,藐视法律,随意以暴制暴,伤及无辜平民。
系统没有回复,停了半分钟才反问:“如果你是墨索里尼,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让成功让她浑身的怒意消散了。
如果她生在当时的意大利,就一定能比墨索里尼做得更好吗?就一定能力压意大利国王和封建势力清缴黑帮吗?就一定能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大搞国民卫生健康工程吗?
任何历史人物的诞生总扎根于所处时代和地区,墨索里尼早年间还是左派人士,加入过社会党,跟导师列宁并肩作战过,为什么他会变成那样?或者说,一战前后的意大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孕育出法西斯主义?
难道真像网友调侃的,“法家思想”主张“乱世当用重典”?
她不想浪费额度,试图穷尽自己毕生所学来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后只能得出一个勉强的结论:那时的社会党,理想和口号是好的,只是被部分人执行坏了,因此导致那些为改变国家现状被吸引进来的人连带着理想和口号一并厌恶,并进行了修正和实践。墨索里尼搞出了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学了法西斯主义,又结合德国的实际情况搞出了纳粹主义。
即使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初衷也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变得更好,在实际操作上,也确实让国民过上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可惜时日不长。
而本该担负起这一任务的德共和意共,实力弱,增长慢,又专注于路线之争和党内外斗争,根本没注意到极端民族主义举起虚假的“爱国”大旗,抢先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一方理念超前但实践不行,一方理念跑偏但执行力一流,双方都是半斤八两。
至于英国……英国既没有先进理念,也没有强执行力,只有一群目光短浅的政客。他们不会尝试突破上限振兴带英,只会尽全力把别的欧陆国家拉下来,在泥沼中共沉沦。丘胖为什么敢扯起反共大旗?除了苏联确实资助罢工工人颠覆英国政府外,也是知道英共实力实在有限,而苏联跟带英中间隔着波兰、德国和法国,完全打不过来,所以可以借着炒作苏联威胁论,赢得一部分党内支持和选票,巩固地位。
她一贯知道政客为了选票可以不择手段,但还是刷新了对政客不要脸程度的认知。
“丘吉尔可是上过教科书的反法西斯同盟三巨头啊。”她瘫坐回沙发上,无意识地晃着腿:“他到底是出于政治目的要反苏,还是自己本来就是反苏魔怔人呢?或者说两者都有?那他为什么又能和慈父坐一起按死德三?”
她很容易就想到了关键词:大陆均势。
苏联显然被划为了欧洲国家。当苏联日渐强大,德苏联合时,他就去找意大利夸法西斯,绥靖纳粹,祸水东引,以破坏德苏联合。而当德三铁蹄踏碎西欧半境,剑指苏联,他又能迅速跟慈父握手言和,按死德三。等德三没了,他又跑去搞铁幕演说,掀起冷战对立,所谓“带英可以没落,别家的日子也不能好过”。
“这就是世家教导出来的政客?就这带英还能撑过二战?”陈澄捋了捋胳膊。
她也即将踏足政界,但她自认做不到丘胖这种程度,要是以后也必须这么干……那还是现在就狗带比较好。
“虽然两党斗争激烈,但英国的文官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官员队伍之一,廉洁、高效、在内阁频繁更迭中维持政府基本运转,不参与党争,只执行政策法令,是很多国家文官制度建设的模版。”
“……”陈澄又打了个哆嗦:“魏玛也参考了英国?”
“是的,魏玛共和国在文官制度上同样参考了英国的文官体系。”它停顿片刻,补充:“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文官制度就已经参考了英国,魏玛只是延续了相当一部分德二时期的传统,甚至人员。”
“???人员?”
她还以为封建余孽只集中存在于军队里,没想到文官里也有一大把。难怪1920年卡普政变那么草率的行动能撑这么久,想必政变后政府出逃期间,有不少文官跟政变军队合作稳定政府秩序吧?这也就不难解释魏玛为什么垮台了,立身不稳、法律有漏洞,执法的人也不尽力,它不凉谁凉?
要是以后让她天天跟那帮封建余孽文官打交道……
她从沙发上蹦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转移注意力。
飓风过后庄园受损不小,她花了大力气重修这栋房子,力图让它跟老拉德森夫妇在世时一样。沙发上还放着索菲娅·拉德森同款楔形文字羊毛毯,屋里的牛头鹿角都买了新的,东南亚铜像全被替换成了中国风瓷器,墙上的挂画则换成了德国画家沃尔特·莫拉斯的乡村风光和森林雪景。
那些油画让她想起了施塔恩贝格,想起波光粼粼的湖面,银装素裹的森林。
她做了几次深呼吸平复心情,将电台换到本地新闻广播。
由于飓风摧毁了佛罗里达的房地产泡沫,本地新闻有不少还不起贷款跳楼的、低价甩卖豪宅的、发放更高利息贷款的消息,她换了好半天才等到点不一样的,来自伊利诺伊州开罗市:密西西比河河堤开裂。
“以老美的基建水平,河堤开裂应该很快就能修好吧?”
“1分钟。”
“行。”
系统笑了:“南北战争后,负责营建密西西比河堤坝的是美国陆军工兵团,他们将大坝修到了38英尺厚,也就是11.58米。”
“似乎还行,”陈澄比划着,11.58米差不多是客厅的宽度:“但是堵不如疏。”
“是的,所以它挡不住洪水。”
“卧槽?”陈澄立刻冲上楼:“乔治!露伊莎!快收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