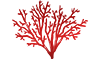一天后,陈澄知道了答案。
柏林大小报纸上都刷屏式刊登一则寻人启事,古斯塔夫·克虏伯的长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失踪,其家族悬赏10万马克征集线索,轰动整个柏林城。
作为最后一批见过阿尔弗雷德的人,陈澄很快就和一群大资本家、庄园管家和女仆等人一起被请进柏林警察局,又眼睁睁看着其他人都很快被释放,只留下她一个被带进审讯室,按在“后悔椅”上等待接受进一步讯问。
一位穿着黑色大衣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坐到陈澄对面,拧开了钢笔。
“维特尔斯先生,在开始讯问前,我再一次提醒您,绑架是违法行为。”
陈澄定定地望着对面的警察,思索这一次又是被谁针对了。
她不算最后一个见到阿尔弗雷德的人,跟克虏伯家族也一直交好,没有仇怨,正常情况下警局不可能把她定为嫌疑犯,除非警局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或是背后有人指使。
“那我也再重申一遍,我是守法公民。”
对面的警察点头,清了清嗓子作为要开始新一轮讯问的预警。
“那么,请您回答一下,1921年9月到1922年4月这期间,您在哪里?”
陈澄的呼吸停了一息。那时候她还在杭州当社畜,后来是以拉德森的身份在外面混,维特尔斯名存实不存。
“这跟阿尔弗雷德的失踪案有什么关系?1922年我还不认识克虏伯家的人。”
“您回答我就行。”
“1921年我刚毕业,一边接手家里的产业和债务,一边找工作。”
中年警察点头,又问:“据我手头的资料,您家只有一座啤酒厂和一座小院,卖掉后刚好还清债务,那之后您在哪里?您买庄园和股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陈澄皱眉,打开光幕查看角色说明。
维特尔斯的身份是随机出来的,只记录了关键时间节点,细节并不完整,因此没有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录。上次小道报纸已经把她的身世扒了个底朝天,如无必要,她不想贸然补充任何细节,以防系统作妖。
她关掉光幕。
“我向朋友借了一笔钱。”
“什么朋友?”
“我的小学同学,一个美国人。”
中年警察拿过放在旁边的一本小册子,大致翻了翻,停在某一页上,点点头:“您在美国待了半年?”
陈澄立刻警觉:“不,当时卡尔在德国,我那段时间也在德国。”
她的护照上没有这段出入境记录。
“您去过威德霍芬吗?”
陈澄一脸茫然地摇头。她没去过,但听说过,这是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中年警察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又问:“1922年6月20日之后,您在哪里?”
“在汉堡考察投资环境。”
“有人能作证您当时在汉堡吗?”
“没有。”
中年警察神情微妙地挑动一边眉毛,露出满意的表情,利落地起身朝外走,走到门边,他回头冲陈澄道:“如果允许您现在接受一位亲友的探望,您会见谁呢?”
陈澄犹豫片刻,回复:“戈培尔吧。”
中年警察“砰”地一声关上询问室的门。
当天下午,她就在拘留室见到了被警察带过来的戈培尔。
戈培尔的眼睛里布满红血丝,整个人疲态尽显。
“柏林警方指控您涉嫌参与1921年慕尼黑威德霍芬农场谋杀案和策划1922年外长刺杀案,您将被暂时扣押。”他将帽子摘下来放到一旁,用身体做遮挡,递给陈澄一张纸条,嘴里一边念叨着:“您需要仔细想想1921年9月到1922年4月,还有1922年6月20日到6月24日的行踪,尽量找到证人。”
这年头还没有监控,凶手可以隐匿行踪,无辜的人却无法自证。
陈澄十分费解:“警方手里有什么证据指向我?总不能想告我就告我吧?”
“以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有三位证人声称在案发时间和地点见过您。”
戈培尔贴心地为她带来两份旧报纸,分别报道了农场谋杀案和外长刺杀案。
陈澄匆匆扫了一眼,发现在农场谋杀案里,一家人早在1921年9月就发现屋里有异响,几次都没找到闯入者,直到次年4月4日被邻居发现一家六口死去多日的尸体,这起案件至今未告破。而在外长刺杀案中,6月24日,拉特瑙早上乘车去上班,路上就被极端分子冲锋枪扫射外加手榴弹攻击,没送到医院就断气了,不过警察很快就抓到了凶手。
“凶手已经抓到了,怎么还能赖到我头上?”
“两个凶手都是‘执政官组织’的成员,经常刺杀国内各级官员,警方认为您是这一组织幕后策划者之一。”
这帮人的幕后指使者是埃尔哈特!一个前防卫军军官!跟她有毛线关系!
“我就不认识几个外交官,怎么能推给我?”
“在您认识施特雷泽曼先生的当年底,施特雷泽曼先生同样遭遇了一次刺杀,这加深了您的嫌疑,不过因为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没有立案。”
这下真是百口莫辩了。她肯定没干过这些事,但她没有人证!
陈澄急得就差蹦起来来回踱步了,仔细想了好一阵才感觉不对劲:“他们把我叫过来问话的借口是克虏伯家的继承人失踪,这跟刺杀案有什么关系?”
戈培尔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承诺:“我将为您寻找最好的律师。”
陈澄点头,目送戈培尔离开后,她才偷偷打开他递过来的纸条。
纸条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汉斯·弗兰克,备注为控方律师,一个是沃尔夫·冯·赫尔道夫,备注为刺杀案人证,普鲁士国会议员。两个名字下面是一个十分眼熟的符号——纳粹的万字符,这两人都是纳粹党员。
很显然,纳粹想把潜在竞争者扼杀在摇篮里,而在众多政客中,她的根基最浅。因为不是国会议员,没有豁免权,她一有嫌疑就被抓了,只能在拘留室里等消息。
“我还以为干掉纳粹这事儿算是十拿九稳了呢。”陈澄倚在座椅靠背上翻白眼。
系统在她耳畔悄悄放起了音乐。
“1921年9月到1922年4月,维特尔斯到底应该在哪呢?”
“你觉得他应该在哪?”
球被扔了回来。
陈澄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刚经历过动乱的家乡应该如何生存。家里还有负债,因此卖掉啤酒厂和房子还债是正常的,投奔朋友也是正常的,那家里亲戚都不来往,全靠朋友接济的人还能去哪呢?
只能是朋友想去哪就去哪。
那拉德森为什么出现在德国呢?
因为她瞎编说拉德森有个姑姑,头婚嫁在慕尼黑,二婚改嫁去了柏林,留下一个儿子。然后姑姑快死了,希望临死前见见这个儿子,于是由他和家人出面劝导这个表哥。所以,维特尔斯应该在拉德森的表兄弟或者继姑夫家。
但她没有设定这俩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现在再补充说明肯定会导致非常大的出入,要么漏洞百出被人发现破绽,要么干脆落实不了。她想到了露伊莎的父母。老拉德森夫妇也出现了设定上的出入,系统的处理方式是直接从物理上抹除bug。
那么,要假设这些人证都已经去世吗?
“人证去世了也没法帮我脱身。”陈澄反复咂摸着纸条上的两个名字:“汉斯·弗兰克,沃尔夫·冯·赫尔道夫,能从这两个人入手脱身吗?”
“汉斯·弗兰克很难,但冯·赫尔道夫伯爵这边可以试试,他很缺钱。”
陈澄咋舌:“他都当到伯爵了,还缺钱吗?”
“他喜欢赌博,再有钱也经不住上赌桌。”
“但是拿钱收买他会显得我很心虚诶。”
系统没有回话,只是关掉音乐,留给她一片隐约的喧嚣。
柏林警察总局就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人声鼎沸算不上什么稀罕事,陈澄也没有在意。她不是第一次经历牢狱生活,有那次被绑架的经历做铺垫,她熟练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考如何应对纳粹的栽赃。
纳粹党对付她的方式非常“政治”,寻找弱点、制造嫌疑、煽动舆论,借刀杀人,是她小看了这个汇聚乌合之众的在野党派,他们只是还没执政过,党争水平并不差。但在她已经获得一部分政党和大资本家支持的前提下,纳粹哪来的底气对她下手?
她再一次想到汉夫施丹格尔。
“洗头佬已经有美国资本扶持了?”
系统沉默片刻,低声道:“从1923年起,希特勒就开始接收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资金支持。”
猜测被证实,陈澄心里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我就说嘛,我掏空两个家族的钱包也就养那么点人,洗头佬一个穷苦出身,怎么能搞出来几十万冲锋队?果然就像祖师爷说的,如果有 300 %的利润,哪怕冒着被绞死的风险也会有人去做。美国资本看不惯我揭穿他们经济殖民德国,打算扶持洗头佬干掉我,然后操控德国……他们根本不在乎二战,因为本土孤悬海外,攻不下也炸不到。”
阿美莉卡这手操作跟英国佬那套大陆均势一样,百年间百试不爽,不愧是父子。
“那么,目的是什么,代价是什么,解决办法又是什么?”
拘留室里有一张靠窗的小床,铺着薄薄的被子。陈澄一屁股坐上去,翘起二郎腿盯着紧闭的大门,想起几年前初见洗头佬的那个夜晚。
“英国和美国离德国远,更希望德国重回资本市场,好好做生意。或者想得更长远一点,已经预料到了资、社两大阵营必有一战,希望将战争控制在阵营边界附近。法国离得近,两家又是世仇,大概希望搅乱德国内政,别让它腾出手来发展。”
美英法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赚钱,如果直接起义再建一次苏维埃德国,暴力清除所有资本,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德国内部资本家的势力强大,周围又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群狼环伺之下,别说起义,动了这个念头就得死。德国不是沙俄,没有冬将军和泥将军,没有战略纵深,没有无限人力,又是值钱的工业国,资本不会轻言放弃。4月份政府通过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后,陈澄光是继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就被警告好几次了,更别说境外资本巨头还没直接下场。
而且,以德共现在的支持率和战斗力,别说对抗右翼势力,跟同源的社民党都闹得不可开交,还占据下风,想干掉所有反对派简直是做梦,更别说对面还有德国防卫军当后盾,开挂上去也是送。
想来想去,最好走的路还是当上德国总理,还得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