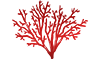柏林警方不可能无凭无据把人关到死,最多等到阿尔弗雷德被发现,她就自由了。陈澄规划得很好,悠哉悠哉地又在拘留室里待了一周,到第二周时,律师果然带来好消息:阿尔弗雷德自己回家了,她也可以回去了。
陈澄被律师和戈培尔一左一右护着往警局外走,好奇心简直爆棚:“他到底为什么消失,又去了哪里?”
“说是心情不好,跑去格鲁纳瓦尔德独处了两周,没通知家里人。”
德佬确实喜欢森林,甚至专为林中独处的感觉造了个词:Waldeinsamkeit,而柏林的格鲁纳瓦尔德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森林,她猜这个回答能忽悠住大部分德子。
忽悠不住她无所谓,对方平安回来就行。
她一脚踏出被称为“红堡”的柏林警局,立刻发现整个亚历山大广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她。救援队不得不用肉身开出一条道路,布赫卢克带着保镖将她团团围住护送上汽车,穿过不断挥手的人群,缓缓驶回公寓。一套流程非常像明星出行,陈澄笑得脸都僵了,只恨自己不会隐身,被人当猴看。
直到关上公寓大门,她才收回假笑,疑惑地看着戈培尔:“我不是让您尽量封锁消息吗?广场上为什么这么多人?正好撞上哪个社会组织搞游行?”
戈培尔看了眼从小书房走出来的夏莉,压低声音:“事实上,您被拘留的第二天就见报了,德共得知消息后,刊文批评对您的不公正处理,声称这是‘政治迫害’,引来了一部分民众聚集在警局门口抗议,我就打算利用舆论向柏林警局施压……”
布赫卢克接过话头:“至于安排救援队,是因为我们收到匿名信称,有人会在您被释放回家的路上刺杀您。”
陈澄心里一时间五味杂陈,向戈培尔和布赫卢克等人道了谢,深呼吸走向自己的书房,结果开门就看到办公桌上又堆了一大堆文件,一口气没上来只想转头逃跑。
没跑成,后路被抱着一摞文件跟进来的戈培尔截断了。
“看起来两周时间发生了不少事。”她只觉得头疼。
“是的。”戈培尔利落地将文件放到办公桌上,抽出一份文档翻开,递到刚坐下的她面前:“您被拘留的两周里,红色阵线联盟和褐衫军在全国各地共发生暴力冲突31起,有17起造成了人员伤亡,其中包括一起在柏林地铁上的枪击案。”
文档里附带一张黑白的现场照片,照片上有三人仰面倒在血泊里。
德共一直都很喜欢在街头跟其他党派和团体物理交流,并随着苏联慢慢恢复元气而越发激烈,跟纳粹撞上也不算稀奇。麻烦的是这种近似街头混混和黑帮的风格会严重影响自身形象,从而流失大量潜在的支持者。
但是,他们是怎么在地铁上爆发枪战的?!警察呢!
陈澄挪开照片,拿过报告翻到有关地铁站枪击案的部分,匆匆扫了几眼。事情缘起于纳粹想要在柏林扩张势力,挑的区是德共的势力范围,双方很快发生火并,几名工人在斗争中被杀。德共于是发起报复行动,冲击纳粹集会现场,又造成了纳粹党成员死亡。然后纳粹党发动报复,在地铁上伏击了德共的一位地方负责人。
报告最后一行备注:本次地铁枪击案导致3名乘客伤亡。
……
来不及吐槽,戈培尔又摊开一份杂志递过来:“还有这篇报道需要您看一下。”
陈澄翻过去看杂志名,《世界舞台》,左翼社评杂志,又翻回来看报道内容,只看了几行就不再往下看。
这篇名为《空中的秘密交易》的报道是老调重弹,披露德国和苏联的秘密军事合作,重点强调德国在苏联利佩茨克建立的空军基地。令陈澄心情复杂的是,报道配图正是从空中俯拍的基地全景,能清晰地看到跑道上停着飞机,这说明他们或他们的供稿人甚至肉身深入苏联侦查了那个基地。
诚实守信确实是美德,自己签过的条约,不管有多不合理,都按头承认,宁可苦了自己,也不要让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不开心,比又当又立还乱撕协议的洗头佬好一点。但眼下德国防卫军就十万人,连国土都守不住,街上暴力冲突都制止不了,不悄悄发展,是等着被法国波兰甚至立陶宛瓜分吗?
陈澄长叹一声。
戈培尔拉开椅子坐到她对面:“杂志总编之一的冯·奥西茨基先生是犹太人。”
她屏住呼吸,抬眼看戈培尔:“所以?”
“冯·奥西茨基先生被判诽谤罪入狱一个月。”
“……”
姑且不论苏德军事合作的正确性,冯·奥西茨基是记者,有说真话的权利,人家没说谎,德国确实违约和苏联搞军事合作了,给他按个“诽谤罪”实在是讽刺。
“但因为他的犹太血统,纳粹党人撰文反犹,获得热烈回应。”
“……”
陈澄一时间没找到合适的表情听这个消息,只剩下满头问号:“且不说是不是诽谤,个体的问题为什么要上升到民族?问题应该是德国记者未经允许擅自拍摄苏联的军事基地,有间谍嫌疑,影响两国外交关系,这跟种族有什么联系?”
戈培尔用眼神制止她有些抓狂的举止:“一位政治领袖不该如此天真。要求每个人都理性思考是非常难的事情,也不好把控,但煽动民众情绪却很简单,口号、目标和指令,越简单、明了、切实,越容易奏效。”
她沉默下来,知道戈培尔说的是对的。
“反犹”很简单,“反对一切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一切”就可以,但要求大家抛开民族偏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具体判断,就太难了。犹太问题涉及到历史遗留、宗教冲突、民族仇恨、阶级斗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双方都有理,双方都不肯退让的情况,没法简单用对错来判断。
她默默盯着杂志上粗细不一的字体线条放空半分钟,挪开杂志拿过前一份报告翻了翻,从抽屉里摸出支票本给戈培尔写了个金额:“慰问一下受害者家属吧。”
戈培尔收下支票,又将其他经过重点标注的报纸和文件一一摆在她面前。
“希特勒试图说服鲁尔区的工业家支持他的政治事业。基尔多夫先生表示,他被邀请和希特勒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会谈,对方希望他提供10万马克竞选资金。”
埃米尔·基尔多夫可是垄断了鲁尔区87%煤矿生产的巨佬!
陈澄血压又上来了:“谁给他俩牵的线?”
“罗赫林先生,他在鲁尔危机时结识了希特勒。”
赫尔曼·罗赫林也是个路灯挂件。
“……基尔多夫先生不会给这笔钱吧?”
“不会。”
她刚松一口气,就听到戈培尔补充道:“不过他给您寄了50万马克。”
“……我不缺钱,退回去吧。”
“他想加入您的无党派联盟。”
“他不是有党派身份吗?人民党还是民族人民党?”
戈培尔贴心地作了修正:“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魁是冯·维斯塔普伯爵先生,不过他们党内分歧比较严重,胡根贝格先生太过激进,导致很多工业家们都脱党了。”
陈澄知道这个党派,它是德国最大的右翼党派,有点极右翼的意思。至于那个胡根贝格更是重量级路灯挂件,纳粹的政治盟友、报业巨头、电报联盟的领袖、《柏林日报》的发行方、几乎垄断德国媒体的“德版默多克”。她去年遭遇的那次“网暴”,背后少不了这人的推波助澜。
这群资本家出身的政治人物玩起手段来比单纯的政治家们高超不少,他们不仅自己集中在几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里,还把除德共外的另外三十几个党派都观察了一遍,分散投资降低风险,提升概率,只等一支异军突起,顺利控制政府践行自己的主张。
在他们的考虑名单上,陈澄不在前列,但也不落后,至少比纳粹靠前。理由很简单,第一,她不极端,成功的几率更大;第二,她自己就是资本家,算是没那么熟悉的“自己人”;第三,她的身家不少,不需要他们花大价钱资助竞选,输了不赔,赢了一定大赚。
她并不喜欢基尔多夫,不过更讨厌胡根贝格。
“就当捐给IFI科研吧,登报感谢一下。回复他,以后会有合作机会的。”
戈培尔记下这件事,又道:“这里还有一份奥地利大使先生给您的信,我没有拆开,不知道内容,也许需要优先处理。”
陈澄不认识这位大使,拆开一看,信还是用德语写的。大致是说7月中旬维也纳发生严重的内乱,左翼份子占领了维也纳大学和法院大厦,纵火焚烧法院,警察不得不进行暴力镇压,造成了伤亡,大使想确认紧急救援队是否接受跨国支援。
“维也纳出事儿了?我们派人去维也纳救援了吗?”
“莱因哈特让波克曼少尉带人过去了,已经返程。”戈培尔翻出巴伐利亚大区救援队上个月的汇报,简单找了找,摊开递给她。
她一看,事情缘起是退伍军人组织的成员触犯了奥地利法律,但被法官宣判无罪释放,释放后居然再犯了,左翼的工人于是联合起来罢工抗议司法不公正。
姑息罪犯确实不行,法律出了问题,左翼要罢工抗议也是正常的。
但为了抗议就把法院烧了也确实抽象,还造成700多人伤亡更加难评。
“烧法院还算有点道理……占领维也纳大学是要干什么?”
戈培尔显然也知道这件事,神情犹豫:“据说,那些左翼工人们认为维也纳大学是奥地利纳粹活动的中心。”
陈澄已经数不清这短短半小时自己无语了多少次,只能感叹奥地利不愧是洗头佬的家乡,洗头佬去大城市打拼了,还不忘提携亲友在家乡搞事。
她点点头,合上文件,示意戈培尔可以离开了。
等书房的门被关上,她才把脸埋进手掌间,长叹一声:“我宁愿回去996,至少日子过得还有点盼头。”
系统又悄悄放起音乐,不过一首歌还没完就被敲门声打断了。
戈培尔去而复返,满面红光:“维特尔斯先生!有通电话需要您优先处理!”
激动到连莱茵兰乡音都冒出来了。
陈澄一脸莫名,站起来一边朝外走一边问:“谁的电话?”
“总理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