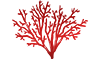一句话搅乱了陈澄一天的好心情。她没心思再赔笑脸,简单吃了点食物,很快就跟冯·塞克特一起坐上返程的飞机。
等飞机离开诺伊德克,冯·塞克特才取下单片镜,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将声音隐藏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会尽力劝说,你也最好不要放松警惕。”
听起来他也觉得这事儿大概率能成?
陈澄学他的样子闭上眼睛,把情绪隐藏起来。
“总统阁下并没有听完我的计划,您觉得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
“等待。”
“……”她想接一句等死。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贴心做了补充,但这点补充也无济于事。
“好,那我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
说完这句,直到飞机穿过波兰把冯·塞克特送回柏林,两人也没再说一句话。
下了飞机,陈澄又坐上来迎接的汽车,继续思考这些天发生的事。
在一个“民主”国家,有钱人登上高位并不是难事,有正常途径组建党派竞选,也有捷径可以选,甚至还有多条捷径。
她选择了有过合作基础,也暗中观察她好几年的冯·塞克特这条捷径,做出许诺,换得对方愿意出面引荐。他是冯·兴登堡最得力的下属之一,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在总统面前的话语权不小。但这并不保险,从午餐时听到的只言片语来看,希特勒也成功跟兴登堡的儿子攀上了关系。
兴登堡未来一定会任人唯亲,现在会不会可不好说。
不过她的胜算仍然比目前的希特勒大。第一,她承诺恢复军队实力并拿出了具体办法,又有海外资产作为保障,而希特勒目前还没成气候;第二,她辖下的武装力量比冲锋队那群只知道街头斗殴的乌合之众要顺眼;第三,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从一开始就存在用冲锋队取缔防卫军的野心,也在啤酒馆政变前后采取过一些行动,两家的小矛盾只是搁置,并未化解,而她的顺从显而易见。
“老冯爷们不是无脑反对一切,只是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怎么措辞。”她在脑海中回想冯·兴登堡的表情和动作:“他们排斥罢工,但他们本身对苏联并没有那么排斥,不然不会同意军事合作。他们不认为苏联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她又放空片刻,想到一种可能:“难道是因为慈父的集权,让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帝制复辟?觉得只是换了位沙皇?”
去年12月,苏联召开十五大,把托先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众元老高层开除出党,基本确定慈父的统治地位,随后宣布的农业集体化又强迫所有农民加入,要求农民贡献了太多,跟魏玛的“苛捐杂税”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如果德国右翼因此不排斥苏联,那可真是黑色幽默了。
黑色迈巴赫压过灰黑色雪泥,停在巴伯斯贝格电影厂大门外,一人高的围栏早已打开,两层簇新的红毯盖住雪泥,红毯不远处,几个穿着黑色礼服的男人恭敬地等待着。
布赫卢克下车打开后座车门,陈澄伸腿踩在红毯上,被微微下陷的脚感引发不太好的联想,停了一息才谨慎下车,一边隔着麂皮手套活动手指,一边往前走。
走到几人面前,她才再次摘下手套,跟这些人握手。
“冯·施陶斯先生、博登海默先生,好久不见。”
两人微笑回礼:“好久不见。”
她学着冯·塞克特脸上微妙的笑容,率先朝里走。
作为整个欧洲电影行业的巨头,乌发电影公司拥有两大制片场地,其中,位于柏林西南,被誉为“德国电影工业摇篮”的巴伯斯贝格电影厂始建于1911年,于1921年被乌发收购,产出了不少精品。
1926年,为了拍摄《大都会》,巴伯斯贝格斥巨资建造了超过5500平米的巨大摄影棚,使得电影拍摄成本急剧上升到530万马克,但票房却惨淡到不足10万马克,资金链因此告急,给了陈澄染指媒体业撬动胡根贝格的可乘之机。
一行人一边走着,一边在CEO的介绍下饱览电影厂布设的各种实景和其他建筑:“这是正在拆除的部分外景,我们打算在这里建一座同期声摄影棚,建筑平面图在这里。”
半秃老男人指着建筑工地旁一块画板,画板上的平面图看起来像躺倒的铁十字勋章,有4个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摄影棚,十字交叉点则是录音室和试听室,勋章东侧则设计有办公区域,还特别标注了绿化带。
德佬搞理工科行当还是很不错的,陈澄不打算对此提出任何可笑的外行人意见,只当旅游观光。既然冯·塞克特对白天的PPT演讲还算满意,那今晚的重头戏就是利用乌发拥有的媒体资源为她今年的国会选举造势,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另一份详细的计划。
几千万马克砸下去,总得见点水花吧?
为了水花能溅起来,被大家注意到,她甚至主动给自己加工作,除了让乌发全力开动,多拍新闻片,多替自己宣传,还奔波于各大工厂、大学、IFI的实验室以及名流沙龙,演讲、拓展人脉、巩固已有的产业,以及争取拉起反纳粹同盟。
2月初,一则新闻在报纸和新闻片里刷屏,成为柏林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勃兰登堡农业园第一批温室蔬菜上市,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劳恩亲临园区采摘一线视察,负责人陪同时,宣布这3天里采摘的蔬菜全部免费赠送给市民,但在视察行将结束时,园区遭到柏林冲锋队的袭击,万幸无人伤亡。
不久,柏林政府宣布取缔纳粹党,柏林警察出动抓捕率先闹事的冲锋队员,行动相关影像被放进新闻片和报纸上,到处传播。
几天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写来道歉信。
陈澄故意来这一出只是为了让该看到这些的人看到,被惊动的其他人都算搂草打兔子。她没有放弃继续争取施特拉塞,在纳粹党内制造分裂,一封措辞恳切的劝说信经戈培尔润色后被寄回施特拉塞手中,自己则应冯·维斯塔普伯爵之邀动身前往歌剧院。
与此同时,戈培尔正在西里西亚拜访著名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盖哈特·霍普特曼,请求对方授权乌发将他创作的剧本拍成有声电影,尤其是反映1848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剧本《织工》和反映柏林社会底层人民处境的剧本《群鼠》。
《织工》是获得导师列宁认可的、塑造无产阶级正面形象的剧本,而《群鼠》则是对方的代表作。这位大佬以“人道主义精神”著称,关注底层,关注现实,支持魏玛共和国,为了避免底层失业工人被纳粹党争取走,她授权戈培尔直接劝说大佬加盟乌发。
除此之外,戈培尔还得负责奔走于各大高校,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
为了争取女性选票,她动用了一切可能动用的人脉:夏莉负责联络底层职业女性,丽泽·迈特纳教授负责联络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产阶级,贝塔·克虏伯夫人负责联络富太太,冯·卡斯特德夫人负责联络贵族女性,初步组成覆盖女性选民的宣传矩阵。
3月8日,柏林街头妇女游行时,她也带着露伊莎下楼转了一圈以示庆祝。经过多方不懈努力,魏玛法律放宽了对避孕产品销售的限制,减轻了对堕胎的惩罚,甚至允许由政府出资资助一些提供避孕指导的咨询中心,虽然没有直接废除堕胎法案,也算一大进步。
当然,她也没有抑制手下的罢工潮,还主动给工人涨了时薪,默许他们带薪罢工。工人们闹得越狠,越能反衬出政府无能,也许不用冯·塞克特劝说,老总统也能意识到换一个有计划有目的能合作的总理有多重要。
预料到本次选举会带来大范围权利洗牌的人不止她一个。
“经济危机论”见诸报端后,这届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陷入了疯狂,通过的法令一个比一个离谱,党争也比此前更激烈。国会否决了德共“对富人提高税率”的提案,却通过了继续向大银行借债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提案,这更是让罢工潮从中部开花,向东南西北四方蔓延。柏林街头游行之频繁,仿佛9年前工人武装起义时的盛景再现。
3月中旬,国会任期将满,冯·兴登堡宣布进行新的国会选举。
4月初,陈澄拿到了各地救援队上报的罢工准确数据,后知后觉意识到这一次罢工的规模比几年前更庞大。光是普鲁士邦就有20万工人参加罢工,还没算上南部一些小州。要是现在再来一次武装起义,会不会比1923年秋天更接近成功?
她收拾好自己,下楼在柏林的街道间穿行,观察参与游行的人和各条街道的情况,失望地发现现在上街游行的全是工人。她又动身去了波兹坦,那里游行的人也不少,但人员身份看起来也很单一。
这说明德共仍然是个工人政党,农民们茫然而麻木,学生们被纳粹党裹挟,小市民和中产阶级则在恐惧德共展现出的强大破坏力: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因为失业聚到一起,不讲纪律和法律,随时准备投入一场街头斗殴,还自称受到苏联“格别乌”的领导要颠覆德国,因而把每一届德国政府当作“法西斯”政权,连同源的,最有可能联合的社民党,也被骂为“社会法西斯”。
与此同时,受到苏联内部争权夺势的影响,德共也亦步亦趋开展了肃清内部的工作,别说反对派了,就连对路线稍稍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撤销职务甚至开除,流水般的失业者因为口号宣传涌入德共,又因为一两句意见不合而退出,可能继续沉沦,可能被纳粹或别的右翼政党吸引,实在是可惜。
20万工人看起来很多,但整个德国有六千万人口,这点数字完全不够看。
还得再等等。
在等待中,选举截止时间一日日逼近,发生在投票站的恐怖袭击事件也越来越多,多方势力杂糅的现政府为工人运动加了一把火。出身民族人民党的内政部长沃尔特·冯·科伊德尔直接宣布要解散德共的“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引发了声势极为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仅在柏林一地预计就有80万人参与其中,甚至可能超过百万。
而柏林警察并不打算示弱妥协,同样策划着更强硬的应对措施。
必须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