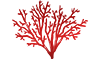晚宴持续到十一点才散场。陈澄昨晚熬了通宵,想早点睡觉,结果秘书们临走前又祭出大杀器——堆成小山的厚文件袋。她又强撑着睡意继续工作,凌晨才上床,想到这一天接收的大量信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不知道希姆莱以前是不是真的跟维特尔斯是中学同学,但今天过后只能是了。同样的,她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好这个总理,但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好在她的最终目标虽然困难,却可以拆分成数个小目标完成,比如先解决上任总理给她留下的几个烂摊子。
她一直想把AFI和IFI合并为“共和国柏林科学院”,为了和1700年腓特烈一世设立的帝国柏林科学院区分开,新科学院专门研究旧科学院不涉及的学科和应用内容。按她的设想,其实是以科学院的名字搞了个工程院,吸纳杰出青年,等时机成熟直接私转公。
私转公不难,难倒她的是第一任院长的人选。
已有的柏林科学院历史悠久,大佬云集,首任院长还是莱布尼茨这种级别的巨佬,新科学院绝对不能差。但她想好的人选要么已经成为院士或接受了官方资助,要么不够年轻,要么就跟“应用科学”不相关。
最后,她只能抽空去各大学视察,看能不能薅一个大佬过来。
第一个去的就是柏林大学。
和上一次造访完全不同,这次一下车,校长就等在主教学楼前,她被保镖簇拥着过去简单握手交谈后,立刻被带往礼堂。对方称已经按她的要求随机抽取50名教师和100名学生,随时可以举行座谈会。
“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待遇还是不一样啊。”
陈澄一边应对聊天,一边感叹,还没迈上台阶,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噼里啪啦敲键盘声响起,好似到了什么互联网大厂,里面窝着上百名正在赶工大项目的程序员,或是周末进了学校周边的网吧,学生们正在里面组团开黑。
但现在是1928年,哪有电脑敲代码打游戏呢?
她带着疑惑盯着缓缓洞开的大门,差点被迎面袭来堪比太阳升起的金光闪瞎眼,赶紧抬手遮挡,同时眯起眼睛试图看清楚这是哪位大佬。
肯定是SP卡吧?这金光跟曼曼的不相上下。
对面站着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黑发男子,发际线颇高,看不出具体年岁,长相也不熟悉,一时半会儿她无法猜到这是何方神圣。不过她奇怪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一群人的注意,陪同在旁的校长立刻介绍:“这是学校的兼职讲师冯·诺依曼先生。”
?临时工背锅法全球通用是吧?老冯爷也有要背锅的时候?
陈澄忍住无语,放下手臂跟对方握手:“您好,冯·诺依曼先生。”
对方也笑着跟她握手:“总理阁下,我本来是负责迎接您的,但刚刚想问题有点走神,没注意您过来了,吓到您了,不好意思。”
“您不用道歉,我并没有被吓到,请您赶紧就坐吧。”
冯·诺依曼让开通道,自己找了个角落坐下。
走向礼堂中间的时候,陈澄悄悄呼唤系统:“我现在没空看角色卡文字,快告诉我这是哪位大佬!”
“约翰·冯·诺依曼,犹太裔匈牙利人,6岁会说希腊语,8岁学会微积分,23岁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参与过曼哈顿计划和电子计算机研制……”
她差点一脚踏空从台阶上摔下去,赶紧顺势装作小跑上台,坐到指定位置。
“你直接告诉我他原本的最终成就吧。”
“他是现代计算机、博弈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领域的全才,精通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
陈澄忽然庆幸自己坐下了,有个支撑身体的椅子,否则怕不是要给大佬表演滑跪。她将目光锁定在坐在门边的冯·诺依曼身上,这位大佬看起来又在发呆,大概是在想深奥的学术问题。
如果他愿意来担任这个院长,什么条件都好说。
她又环视四周,按她的要求,随机抽取的教师和学生已经将她的座位环绕起来。
“各位教授、讲师和学生们,下午好,我是路德维希·维特尔斯。我今天来柏林大学,是想听一听接受高等教育的老师和学生们如何看待柏林科学新院,以及为新院寻觅一位年轻的院长。因此,我不会发表演讲,我更希望您们能向我提问,表达您们的想法。”
一开始,大家提出的问题还比较常规,诸如:“为什么要设立新的科学院?”
“为了给青年人才更多机会,为了弥补旧院只关注部分学科,只关注理论研究的不足,让科学发现更快应用,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
“为什么要求院长必须年轻?”
“因为我们必须证明青年有能力有实力让德国变得更好,能顺利完成接班。”
“怎么样算年轻?”
“38岁以下,20岁以上,也就是1890年-1908年出生的人都可以投简历。”
“新的科学院是怎样运行的?”
“以学科大类和课题小组的形式运行,每一门学科大类每年能获得不同金额的科研经费,如何分配取决于学科负责人和课题组组长,组长们需要撰写实验计划,通过审核后立刻拨款开始实验,技术成果通过验收后立刻申请为专利,授权或出让专利所产生的收益30%归发明者个人,20%作为课题组专属活动经费,50%归科学院。”
然后画风就开始跑偏了。
有人问:“我能不能伪造一个永动机来骗经费?”
“……您能造出来的话,我会酌情考虑把它放在科学院的展览馆里,将门票收益的50%作为奖励返还给您。”
有人问:“科学院院长可以只做研究或者只做管理吗?”
“不可以,院长必须是某一个学科的负责人,必须亲自带至少一个课题组。这个职位与学科负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一部分工作时间将从科学研究中抽离,转向理论学习、概念验证、人员培养和资金分配等行政管理工作,当然,可以配备相应的助理。”
在问完薪酬福利等内容后,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心动了。但随机抽到的教师和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不符合要求,开始抗议:“为什么要把年龄限制到38岁以下,您这是歧视!”
“……因为我希望给青年人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经验更丰富的教授们同样可以在学校里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
“为什么把年龄设置在20岁以上,20岁以下就不是青年人吗!”
“……年纪太小的话,我还是建议他能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否则择优录取时很容易被更优秀的人刷下来,浪费时间。”
“您为什么不自己当院长?”
“……我还有很多别的工作要做,而且,我无法成为某一个学科的的负责人。”
“您为什么不直接任命一个,而要让大家投简历筛选和面试?”
“这是出于机会平等的考虑。”
要不是考虑公平,她肯定直接任命SP卡冯·诺依曼。
好不容易扛到中场休息,陈澄终于有空查看起那张SP卡的信息。
卡名“最强大脑”,主卡面上的冯·诺依曼正是她刚刚见到的样子,光看外貌很难想象他出生于1903年,这会儿才25岁。卡面浮印是一座比人还高的巨型机械,有很多圆柱形和长方形铁片,无法辨认具体功能。沿着巨型机械的外缘,一串由“0”和“1”组成的不规则数字符构成了卡面边框。
陈澄翻过卡面,很意外大佬童年时清秀可爱的程度与曼曼不相上下,再联想到大佬精通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不禁感叹变秃果然能变强。
一只手进入陈澄的视野,在她面前放下一杯咖啡和一份小甜点。对方顺势坐到陈澄对面,清了清嗓子:“总理阁下……”
“迈特纳女士?”陈澄赶紧关掉系统:“您刚刚坐在哪里?我都没看到您。”
“我没有被抽中参加座谈会。”
“倒也不必那么严格,您待会儿找一个空位子坐下就行,或者有什么想问我的,现在就问也可以。”
虽然不是可收集角色,但学术大佬在她这里都是有优待的,何况她这次竞选对方也出力不少,算得上盟友。
丽泽倒也开门见山:“您不是竞选国会议员吗?为什么要着急去做总理呢?”
看来她暴露的问题还挺多,普通人都能发现她上位有问题,聪明人更是一眼看出她的行为前后不相符。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她不向政客坦白,但对朋友则没必要过度隐瞒。
丽泽犹豫了几秒,果断决定问出来:“您会认为经济危机是犹太人造成的吗?”
陈澄愣住了。
她反复尝试观察丽泽的神色,只能感觉到对方满怀强烈的不安,但无法得知这股不安来源于哪里。这位大佬不是只专注于物理学术研究和学术女性地位平等吗?
“您为什么会这么想?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过度自由放任,导致供需关系失调的体现,是不懂节制的资本家们造成的,跟某一个民族没有直接关系。非要说有点关系的话,那也是犹太人里的资本家参与了经济危机的形成和恶化,不能说完全由犹太人造成。”
“那您会限制犹太人接受教育、担任公职,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吗?”
陈澄一脑门问号:“不会,我保证我肯定不会。”
丽泽松了口气,犹豫片刻,低声道:“是这样的,我是犹太人……”
她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是位出身还算富裕的犹太人。这两年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一些小政党正在疯狂鼓吹各种反犹极端政策,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柏林大学虽然是象牙塔,但象牙塔没有门,各种风言风语都会在校园里掀起波澜。一旦被坚持反犹主义的政党执政,她就不得不考虑放弃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教职,逃离德国。
陈澄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有政党在校园里鼓吹反犹?”
“是的,就在竞选投票的时候,有人宣称犹太人不能获得投票权,说我们会选出一个犹太总理,窃夺国家权力。”
“……”
她好想回怼,但看着丽泽的神情,又张不开嘴,只好再次承诺自己绝不会搞种族主义那一套,让丽泽放心。
散会后她主动去找了冯·诺依曼,对方同样顾虑重重,没有立刻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