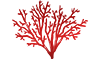祸福相依,养伤期间她每天都能收到好消息,非要说产生了什么坏结果的话,大概就是老的小的看她看的更严实了。
夏莉只能瞒住露伊莎一时,等她回柏林修养就瞒不住了,好在她恢复得还行,小姑娘只是更加喜欢赖在她的床边和书房,不至于哭红眼睛。倒是卡斯提李奥尼送来了她意料之外的深切关怀——一辆防弹定制版迈巴赫。卡大叔大概不清楚刺杀事件的细节,以为她是行驶途中被袭击,特意加强了车体厚度。
陈澄赶紧写信解释并婉拒礼物,转头开始头疼新的秘书人选。
养伤这段时间都是夏莉充当她的秘书干活,有此前多年相处打底,一点纰漏都没出。但夏莉本身有补习学校的工作,又是社民党议员,玛丽女士看好的人,如果让她回来接任秘书工作,多年培养就将前功尽弃。
思考数日后,陈澄决定去征求夏莉本人的意见。
夏莉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继续担任她的私人秘书,还不无调侃地道:“这难道不是巩固您跟社民党联盟的好机会吗?”
陈澄立刻就被说服,态度强硬地给冯·施佩打了招呼,让他们接纳新同事。而夏莉也不负所托,正式上任没多久就带来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冯·诺依曼确认就职柏林科学研究院新院院长,另一个是沙特的油井已经建设完成。
合成聚乙烯需要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但德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聊胜于无,煤炭又集中于鲁尔和西里西亚,且被私人垄断,因此聚乙烯试验成功后一直没有大规模生产。现在葡萄牙的油轮已经就位,只待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沙特的石油运来汉堡,加上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回归,她就兴奋地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这个消息。
廉价能源的大量供应和新消费市场的开辟对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对部分工业家,尤其是煤炭矿山的所有者和重金购买煤转化专利的企业来说不算好消息。短暂的兴奋后,有人提出了担忧:“它会与本国的煤炭企业竞争能源市场,很可能影响它们的生存。”
“各位不必局限在煤炭企业角度考虑。”她已经想好说辞:“如今我们欠着一千多亿马克的债务,财政赤字高达70亿马克,还有大量建设资金缺口,必须进行开源,也就是增加政府收入。而增加政府收入只有四条路,第一,提升税率增加税种;第二,发行债券;第三,对外借贷;第四,开办国企盈利。”
“选第一条,现在国民背负的税务已经很沉重了,继续加税只会逼得民众生存艰难,最终起义反对政府;选第二条,民众对债券的兴趣也在降低,上届政府的5亿马克公债还没填上,又有多少人会再次购买?选第三条,我们对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的依赖已经很严重了,还要再加重吗?一旦美国经济崩溃,我们将深陷旋涡,无法自救。”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开办国企来盈利,而且我们需要更多国有企业。”
众人沉默不语。
要按以往,她肯定绕场逡巡,加强说服效果,可惜现在她连站起来都费劲,只能老实坐着观察与会众人的表情。
“从长远来看,煤炭不是无穷无尽的,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必须提前准备好新的能源供给渠道;另外,燃烧煤炭带来的污染实在太过严重,鲁尔区的水源、土地、空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威胁着千万德国人的生存安全。除了石油,我们还需要发展电力、水电、海上风电、潮汐……我们需要兴建更多发电厂。”
“我们在北部已经有一座潮汐电站了。”
“这不够!”她伸手指指戈培尔:“我有一个详细阐述这些基础建设内容的‘四年计划’,会写成备忘录分发给各位。简单来说,我打算启动‘大众化’计划。所有在我国市场上销售的外国商品,都要有对应的国产品牌;所有当前只有少部分人拥有的商品,都要尝试推广给全体国民。”
洗头佬虽然有很多错误,但早期一些应对大萧条的政策还是很不错的,其中就包括推广国民轿车和配套高速公路,据说当年洗头佬在任时修建的高速公路有的到现在仍在被使用。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澄决定批判性借鉴一下。
扫了一眼众人的神色,她继续游说:“这两个计划的目的很简单,经济是靠生产和消费驱动的,我们不能只考虑一方面,现在生产已经趋于饱和,外部出口又遭遇其他国家的竞争,在等待内部技术升级的同时,我们需要拓展内部消费需求,丰富民众的生活。”
这套逻辑其实不难理解,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她中学时代就学过的课程,现在只是在做文综大题而已。麻烦的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除了社民党会无条件支持外,其他人多少有点顾虑。
试点开始后,她听说有人私下把她的“无党派联盟”称为“德国劳动党”。
听起来阳光明媚得很。
短暂的沉默后,施特雷泽曼转入自己的话题:开启与协约国各国,尤其是法国的谈判,以求彻底解决赔款问题和撤离莱茵兰。他提到了一份可能被签署的国际公约,原则上,缔约各方将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推行的工具。
如果说陈澄的规划还有哪些不足的话,大概就是所有的计划都是长期计划,无法短期见效,更无法立刻解决迫在眉睫的一些问题,比如莱茵兰仍有法国驻军,比如《道威斯计划》仍在无上限的收割德国经济,再比如,跟波兰的贸易战和敌视状态。
不管这帮列强实际上心里藏着什么小九九,表面上他们还是愿意和平的,至少在欧美间维持和平。大家都是值钱的工业国,打一仗伤筋动骨,实在没必要。
但即使是推行表面的和平也很艰难。经过一战这么惨烈的战斗后,列强,尤其是法国,迫切希望阉割德国,让它失去再一次发动战争的能力,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剥削魏玛,往德国周边放一堆傀儡国,波兰、捷克、还有巴尔干大杂烩。
本来这个计划还挺靠谱,可惜他们低估了波兰。
波兰持续在德国东部施加的压力使德国的和平主义者饱受内部排挤,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协约国希望通过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迫使德国真正履行裁军计划,但波兰对德国领土的觊觎导致从防卫军到民众都担心入侵,不肯真正放下武器,而秘密军事力量的存在又使得协约国担心德国正在积蓄力量报复,从而继续施加压力。
施特雷泽曼已经多次向法国人释放和平信号,从陈澄跟他几次沟通来看,老爷子虽然不同意放弃修改东部领土边界,但还是希望以和平谈判的形式解决。他不想打仗,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东普鲁士孤悬海外,公路铁路都不通,只能坐船或飞机过去。
对此,陈澄只能表示难评了。
她不清楚当时协约国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这样的边界划分,但这样划分德国确实毫无道理。如果只是为了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完全可以从边界地区划,比如东普鲁士东部靠近立陶宛的梅梅尔地区,如果是为了更好地限制德国,完全可以直接把整个东普鲁士都割走,现在这样的划分方案实在是……一股搅屎棍的既视感。
她猜是带英提的,为了阻止德波和解,进而牵制法国的注意力。
可惜现在再找带英算账也不能了。
施特雷泽曼只能将矛头对准防卫军和社民党,言辞激烈地表示,本来1926年他已经争取到法国撤出莱茵兰、归还萨尔、撤销军事监管等承诺,结果当年底防卫军跟苏联的秘密军事合作居然被社民党在国会当众披露出来,导致法国人的态度转变。双方打了一年半嘴仗,没半点进展,本月底他又将前往巴黎,重提撤军问题和修改赔偿计划。
以米勒为首的社民党人则坚持指控防卫军的秘密重整军备,尤其反对在威廉·马克斯手里已经通过的海军预算,PTSD一般提及一战前的海军扩张计划。
陈澄意识到这又是前任给她埋的大雷,心情复杂地看着两个老爷子涨红的脸:“这次和谈大概也没什么效果吧?”
“成果不算丰硕,但积极意义还是有一些的。”
系统正经的语气把她逗笑了。
“我现在在这里坐着都算积极意义,因为之前受伤只能躺着参会。”她悄悄看了眼被cue到的社民党人和国防部长格勒纳:“所以有什么积极意义?”
“你肯定会签那份和平裁军公约对吧?”系统漫不经心地问着,却没等她回答:“所以他们也能达成点协定,比如举行正式谈判研究撤军问题,比如组织财政专家组成委员会讨论赔偿问题,再比如,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
陈澄的记忆跳到久远的1923年,想起德共的那次十月大起义。
“原来大家都差不多,文山会海。”
“只要涉及多方利益,只要还坚持民主,文山会海就是无法避免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受到不同的成长经历影响,并被自己的想法和目的支配,有个争取的机会,有个表达的舞台,谁会放弃呢?”
说的很有道理,陈澄点头:“下次别说了,说的再好听也掩盖不了你在劝我搞独裁。独裁有什么好?我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导致很多人失去生命,觉都睡不好。”
她想起汉斯·哈克曼,又隐约从那团红色橡皮泥上看出弗里茨·埃斯勒的脸。最后,她被米勒的声音唤回神:“如果总理阁下无法出席日内瓦的磋商会议和国际联盟大会,请允许我代劳。”
看起来很想去的样子,她同意了。
施特雷泽曼面露惊讶,一散会就拉着米勒私聊。
陈澄慢慢起身,一边收拢今天表决的那些草案资料,一边听戈培尔说话。
“柏林警局敲定了扫黑纪录片的叙事主角,警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先生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出镜拍摄。”
他递过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身材异常高大,穿着军装同款制服、马裤和长筒皮靴,戴一顶奇怪黑帽子,腰间挂着复古的长剑,看起来能无缝衔接隔壁防卫军军官。
“形象不错,麻烦这位先生出镜的时候换掉帽子,带上手枪。”
她将照片还给戈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