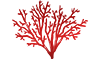其实施特雷泽曼知道施拉格特的故事。
当时英国人除了吐槽法国人的暴行,也吐槽过德国人外宣没跟上,说出诸如“如果他们在鲁尔对你们的所作所为发生在法国,全世界都会对你们口诛笔伐”这类金句,所以施特雷泽曼才会重视乌发的破产重组,让冯·施陶斯派人联系陈澄。
只是他当时忙于外交事务,而冯·施陶斯更倾向于将乌发交给胡根贝格。直到她入狱期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们在议程外讨论了乌发的债务问题,打算制定一项贷款计划防止电影业被“美国人控制”,施特雷泽曼当众提起她的名字,获得时任总理威廉·马克斯的认可,才有博登海默那次前后脚的登门。
他们确实有所图谋,但那不过是拖到不能再拖了才进行的补救。
《安娜伯格山的英雄》上映当天,施特雷泽曼特意出院跟陈澄一起参加了首映礼,在观影前详细跟陈澄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如果说她对魏玛的政客还有那么点好感的话,那这些好感值大半都是施特雷泽曼刷的,人家是真·爱国资本家,为魏玛奔走呼号到死。
黑白灰的电影画面里,施拉格特在自由军团的老上级豪恩斯坦站在镜头前发表演讲:“……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征程尚未结束……把我们的人民从内外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是我们心中的远大目标……不要安于现状,不要羡慕过去……”
镜头上移,露出一堵墙,再下移时,豪恩斯坦换成了施拉格特和法国占领军。
“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我的德国问好!”
一声枪响,饰演施拉格特的男演员倒在血泊中,眼睛仍然睁着,睫毛颤抖,弥留的刹那,回想起自己听从德皇号召弃文从军的那天……
陈澄从没想过黑白电影也能这么动人,忽然为自己当年没能结识这位英雄而遗憾,也许当年同样穿梭在鲁尔区某座城市时,一个平常的午后,他们曾经擦肩而过。只是他被抓时她正好离开鲁尔,无缘得见。
这部电影是乌发制作有声电影的一次尝试,她本来是想拍出来纪念英雄,现在却用来搭配对小施蒂内斯的审判,勾起民众对鲁尔危机期间的回忆。为了达到效果,她掏钱补贴一半票价,要求全国影院,乃至属于乌发的海外影院也在近日陆续上映,人为炒热度。
参加完首映礼,她还得等几天,等媒体的跟进让电影带来的热度逐渐发酵,再以更有话题度的方式开启审判——推迟外事访问,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搭建露天法庭。
开庭当天,整个亚历山大广场上被堵得水泄不通,柏林市民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只恨看不到细节,有很多人甚至爬上大树,就为了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靠保镖开路,陈澄才顺利穿过人海,抵达庭审现场。
人群中心是一小片空地,放着三张长桌,分别是法院、辩方和控方,每张长桌旁都放着话筒和音响,但扩音效果一般,加上外围人群正在激烈讨论,里面的人要很大声才能让自己的声音真正被人听到。
现在正进展到人证陈述阶段。
一位妙龄少妇站到话筒旁,举起自己的身份证件在众人面前晃过,又向一位路德教牧师发誓自己每一句话都是真的,然后才开始控诉:“我丈夫家里的铁匠铺传承了快一百年,专给人打菜刀匕首为生。鲁尔区被占之后,稳定的铁矿石和煤炭都没有了,生意难以为继,不得不宣布破产。施蒂内斯先生宣称会收购我们的铺子和工具,用600万马克。”
少妇哽咽了一下:“但等他给钱时,600万马克已经不值钱了,连一块面包都买不到,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她倒没有细说如何另谋出路,不过也不难猜。
鲁尔危机前后,多少女性被迫下海给全家挣口粮,根本统计不过来。
明面上施蒂内斯所有收购合同都是合法的,但实际上大部分是趁着人家破产恶意压低收购价格,然后延期付款等待货币贬值,再轻飘飘地使用废纸一样的马克达成交易。还有一部分路灯挂件则更过分,直接使用私人银行的支票付款,然后宣布银行破产,无资产被清算,却把人家毕生经营的公司骗到手。
前者可以通过规范合同内的付款期限和违约金来规避,但后者却难以避免。一战后德国的银行不是倒闭就是被协约国监管,想规避私人银行印钞和发售债券,就得对金融领域进行全面清算,而想对金融业出手,就得先让协约国放松对德国的经济监管。但法国人坚持先履行新的赔款计划才放松监管,6国外长和代表还在巴黎、日内瓦和海牙三地辗转扯皮。
当年的情景,跟后来1926年葡萄牙货币体系崩溃何其相似。只不过葡萄牙资金缺口小,被注资后缓慢落地了,而魏玛资金缺口太大,“啪叽”一下摔进了美国资本的怀里,成为待宰的羔羊。
陈澄站在这里,看一个又一个人证走到话筒前陈述自己家是如何一夜赤贫,如何从还算富裕的中产变成等待救济大军中的一员,如何因生活难以为继而忍饥挨饿、日夜不停地打工,如何收敛自杀的亲人,留下的孩子如何靠社会救济长大,又继续当学徒工。
就像1923年夏天那颗贯穿左胸的子弹,又一次穿过她的胸口,带起呼呼风声。
那年的她把钱花在哪了?
花在购买粮食和斯柯达厂的股份上了。
如果当年直接买凶干掉施蒂内斯,会有多少家庭幸免于难呢?
她想起扬克给她的那些名单,不止施蒂内斯,还有很多人,杀是杀不完的。
归根结底,德国自身潜力太小,又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就像一颗埋在心脏附近的炸弹,人们或许不会在乎路边的地雷,但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对心脏的直接威胁。
除非到处都是威胁,大到无法全部顾及。
中午,救援队开始给参与露天法庭的人们发放便餐,一碗土豆浓汤、几根香肠、鸡蛋煎吐司片配芦笋,吃完接着审。直到夜幕降临才停下。
这场审判光是控方人证第一批陈述就持续了5天。5天上百人的血泪史听下来,法官和双方律师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临近五一劳动节,各地德共成员都在陆续往柏林赶,当天下午就有德共成员撰写请愿书,号召民众签字判处这批资本家死刑。第二天,一份名单被曝光,上面清晰记录着鲁尔危机期间一些资本家如何通过货币贬值掠夺同胞财富,请愿死刑的名单骤增。
一旦民意被煽动,要控制住就很难了。陈澄无意控制这股请愿潮找骂,但也不想让韭菜就此断根,她已经准备好措辞,在悄悄公布名单后,还要去补上最后的漏洞。
兴登堡。
正值春天,再直男的庄园里也少不了鲜花点缀。奥斯卡带着陈澄穿过大门,走向书房,一开门,正见到冯·兴登堡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听仆人给他读书。
“父亲,维特尔斯先生来了。”
冯·兴登堡睁开眼睛,示意仆人停下,给陈澄上茶。
“有事?”
陈澄往里走了几步,低声道:“总统阁下,有件事需要请示您。”
“嗯?”
“施蒂内斯家族涉及不正当竞争,可能被判拍卖家产缴纳罚金,我想留下他家的航运公司作为保障非洲计划的备选。”
冯·兴登堡站起身,居高临下地望着陈澄:“不用葡萄牙那家公司了?”
“用,当然需要使用葡萄牙的油轮,但不能只使用葡萄牙的油轮。因为油轮需要海军护航,往返频率过高,会引起间谍的注意,需要更多船只分摊注意力。”她适时抛出秘密作为交换:“我在芬兰也购买了造船厂,往后会有更多船只参与到‘重返非洲’计划中。”
“你会得罪那些富豪们。”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保障德意志复兴。”
她尽力伪装成狂热的爱国者,但从老总统脸上看不出来信没信,只能从问话中确定对方仍有顾虑。
“我打算给他安上间谍的罪名。”她又递上把柄供对方拿捏:“商人永远更看重利益,在世界大战中赚足了资产的商人不会满足于和平,会想方设法再次挑起战争。施蒂内斯先生虽然是德国籍,但在世界大战中资产足足翻了30倍,又靠着鲁尔危机登顶德国首富,他的儿子不会满足于破产后勉强维生的日子,会想办法再次挑起战争。”
其实施蒂内斯是不是间谍并不重要,或者说,是不是施蒂内斯家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个没人能反驳的罪名清算一小撮资本家,瓜分掉他们的财产,打开突破口。只是施蒂内斯正好是那只出头鸟,又因破产而成了软柿子。
她已经为这场判决的终章定好日期:五一劳动节。历史上的这一天,德共违反柏林警局的禁令举行游行,遭到社民党左吉贝尔局长下令的暴力镇压,共造成33名平民死亡,近200人受伤,史称“血腥五月”。
为了稳定内阁,也为了不给纳粹出头的机会,她不能强迫普鲁士内政部取消这一禁令,但她同时也知道自己无法劝说德共取消游行,只能采取别的方式减少警察和工人双方参与活动的人数。
如果台尔曼接受这种方式,她不介意每年4月都噶一次韭菜做贺礼。
“法官不一定会信。”冯·兴登堡自然不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绕,问:“证据呢?”
“只要彻底搜查,总会找到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年她也被纳粹用这招诓进局子,差点成了谋杀案重犯,现在她正在学以致用。摸着洗头佬过河,虽然恶心,但好用。
“你要说他是哪国间谍?法国?”
“不,英国。”
法国人固然想让德国死,但招式往往直来直去,不太可能收买间谍。
冯·兴登堡没有挪开视线:“我听说你让派往利比亚的那支小队也学了英语?”
“是的,他们也学了法语,这是为了扰乱敌人的注意力。毕竟,大家都知道,英国和美国都不想要一个和平的欧洲。如果万一被俘,他们会说的语言越多越杂,越能证明幕后主使身份不一般。”
让意大利怀疑在背后挑事的是伪装成法国人的英国人,比伪装成法国人的德国人,更贴近英法百年友谊的大背景。
冯·兴登堡点头,失去兴趣。
“你放手去做吧。”
他坐回沙发上,阖上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