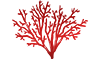送走两位夫人,陈澄又致电格勒纳,详细讨论如何应对纳粹党对防卫军青年军官的引诱和渗透,等格勒纳冷静下来,再次站到内阁这边后,她才挂断电话。
5月底,陈澄收到汇款通知单,有300万美元汇入了她在瑞士银行的账户。
这个账户是当年在庄园囤粮时开设的,已经很久不用了。她以为有人汇错款,准备处理退回时,又在邮箱里发现一个精美的小盒子和一封信,这才知道是沃伯格给的酬金,他打来了第一阶段的款项,以及附赠礼物。
小盒子里面是一枚钻石戒指,大约5克拉。她确认这不是需要收集的物品后,就扔在抽屉里不管了。至于那300万美元,她将用在建设几所飞行学校和下个月全国青年社团创新大赛评选的奖金和经费上。
青年社团创新大赛是去年她刚上任时提出的计划,一年一届,目的自然是给年轻气盛精力没处发泄的少男少女们找点事做,以免他们投奔纳粹。经过两位夫人的提醒,她又打算大肆宣传这一比赛,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本以为这群小年轻们也就是搞搞滑翔机、木轮船的水平,没想到决赛还没开始,戈培尔就把一本薄薄的册子放到她面前,郑重地表示:“这个小组一定是第一名。”
陈澄一看,书名《通向航天之路》。
卧槽???
人类才刚驾驭飞机几年,这就想着冲出大气层了?
她翻开小册子,第一页介绍了作者,是德国人,但出生在奥匈帝国境内,参加过一战,战后试图申请个博士学位,但论文被毙了,此后一直在罗马尼亚当中学数学老师,前年听说德国成立了宇宙航行协会,于是回到德国,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现在,他代表宇宙航行协会参加第一届德国青年社团创新大赛,交出的参赛作品就是一枚两米长的火箭。
陈澄低估了老牌工业强国的青年素质,他们真能手搓火箭!
她顾不上手头的工作,带上书就直奔柏林郊外给参赛选手设置的试验场。
为了鼓励青少年均衡发展,本次青年创新社团没有区分赛道,只划分了8个参赛区,初赛晋级完全靠同地区其他参赛选手推选,每个地区最多推选3组来到柏林参加复赛,每个地区三选一进入决赛。为此政府专门在普伦茨劳贝格开辟了一块试验场,由小组自行申请试验场面积。
眼下参加决赛的24个小组已经全部入驻,空旷的草地上盖起了二层小楼作为选手宿舍,木棍和绳索组成的简易篱笆分割着大大小小的场地。
陈澄一迈进试验场,就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随后是一连串提示音。
“有好多可收集的卡!”
她兴奋地循着提琴声往前走,很快就看到一位穿着大红长裙,身材高挑的少女正背对着大门翩翩起舞,午后微风拂过发丝和裙摆,好似枝头飘落的花。
少女一个旋身,裙摆散开如百合,又聚拢到小腿旁,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她又绷直脚尖,跳跃着几步走到鼓掌的陈澄面前,冲她弯腰行礼。锋利的美貌如同一柄划破微风的刀刃,耀眼到令人不敢直视。
“总理阁下,您好,我是莱妮·里芬斯塔尔。”
陈澄恍惚着跟对方握了手,环视周围,没看到小提琴,也没看到任何能放出音乐的设备,最终确认是这张角色卡自带的音效,就像冯·曼施坦因自带防空警报,冯·诺依曼自带键盘敲击声一样。
这是她收集到的第一张女角色卡,一位又美又飒的小姐姐。虽然乙游出现百合线有点离谱,但如果是这样的姐姐,她只想说:“我可以!”
陈澄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看航天小组的,兴奋地跟在里芬斯塔尔旁边不停地问:“您也参加这场创新大赛吗?您代表哪个地区?您的作品是什么?”
还是戈培尔碰碰她的肩,她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我代表柏林地区参赛,我的作品是一部电影。”
里芬斯塔尔笑着将她让进场地里,展示画到一半的电影海报:“《帕吕峰的白色地狱》,讲的是一名男子爬上12000英尺高的山峰寻找迷路的妻子,另一对夫妻跟他一同完成攀登的故事,全实景拍摄,已经拍完了,打算在10月份上映。”
海报上是三个正向高峰发起攀登的身影。
“很有趣,等上映了我会去看的。”
陈澄还想跟小姐姐聊聊,可惜戈培尔已经快速要到了里芬斯塔尔的通信地址,然后拉着陈澄往旁边的大块空地走。
“您可以给里芬斯塔尔小姐写信。”
“啊,确实。”
陈澄一边走一边打开图鉴,“美丽捕手”莱妮·里芬斯塔尔,是一位SP金卡角色。
主卡面上的里芬斯塔尔拥有近乎完美的面部轮廓,蓬松着一头金色卷发,眼神冷静,鼻梁挺直,上嘴唇是完美的“M”形,倾斜卡面后,挺直的鼻子变成了上身,起伏的唇形变成了芭蕾舞裙裙摆,她手臂高举,一条腿向后抬高,高昂头颅,像一只起舞的天鹅。跳跃的音符波浪状环绕着她,浅蓝的颜色温柔得如同清澈湖水。
美好的事物总能让人心情愉悦,陈澄整个人都舒展了。跟着戈培尔往前走,她很快就看到一片场地中央那根竖起来的火箭,以及围绕火箭站着的三个男子。
小团队里最年长的一位走过来,跟陈澄和戈培尔握手。
“总理阁下,部长先生,您们好,我是赫尔曼·奥伯特。”
“我是沃纳·冯·布劳恩。”
叮咚——一张SSR卡解锁。
“我是约翰内斯·温克勒。”
陈澄甚至没来得及看卡面,打完招呼就快步走到火箭旁,绕着这根火箭左看右看。除了尺寸过小外,这根火箭外形上跟电视里看到的单体火箭已经大差不差了。
“你们的火箭能飞多高?”
三人面面相觑:“初赛时还没成功,我们正在改进。”
陈澄点头,这很正常。要是成功了,早就该量产、迭代、商业化了。
“会成功的,我很看好你们。”她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这根火箭,忍不住开始畅想:“把它放大,把卫星送上天,这样就可以开发卫星导航、卫星电视,卫星通讯,可以打电话看电视剧……然后加助推器,改载人舱,能把人送上太空!登月!建空间站!”
她看着几人:“你们这项研究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没经费?”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当然经费也是重要的。”
技术上的问题她就帮不上什么忙了,不过经费她可以解决:“我个人可以资助你们50万美元,另外需要哪些专家教授的指导、或者需要场地什么的,尽管写信给我,我尽量为你们争取。”
奥伯特挠挠头:“您能支持我们,我们就很开心了。您也认为未来我们人类能依靠火箭进入太空?”
“当然!不过先不急着载人,可以先在近地轨道多架设一些人造卫星,解决通话不方便、出门会迷路、没有太多娱乐项目的问题。”
“人造卫星?”
“对,就是用火箭带到近地轨道上,绕地球运动,从太空向地球传输信号,或者当地球上远距离之间信号的中转站。”
陈澄恨不能掏出手机给大佬展示卫星地图,可惜她没有手机,只能摸出兜里的支票本和笔,给这个小组赞助经费,希望大佬赶紧搓出来火箭:“不够再来找我,这是我个人赞助的,跟本次大赛的奖金和经费不冲突。”
捏着这张支票,三个人面面相觑,迟疑着道谢。
陈澄挥挥手,打算再去看看其他小组,却被冯·布劳恩叫住:“总理阁下,您设想中的火箭是怎么样的?”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
她回头,想了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按照电视里见过的火箭外形简单描了个边,然后凭印象划分区:“火箭本体、助推器,上面有个整流罩,下面放个逃逸塔。”
冯·布劳恩没有管这张儿童简笔画,又问:“您认为火箭的动力应该是什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摆脱不了引力,飞出去一点距离就炸了……”
“那不就成导弹了吗?”陈澄把自己说愣了,迅速点开冯·布劳恩的卡查看生平事迹。果然,这位冯·布劳恩男爵就是为德三研发v-2导弹的大佬,而v-2导弹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弹道导弹。
放任他再做下去,好好的载人火箭就得变成战争武器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安全为上。”她咽了口唾沫,想到冯·布劳恩现在才17岁,莫名有些心慌:“探索尖端科技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您可以慢慢尝试您想做的东西,国家支持青年人的创新。”
“但是弗里茨·朗先生邀请我们为他的新电影制作登月火箭模型,我们想要做到最好。”奥伯特热络地凑过来:“时间很紧,他希望赶在今年冬天上映,如果您也对火箭感兴趣,能说说您的想法吗?”
她听说过弗里茨·朗,乌发电影公司的台柱之一,《大都会》的导演,确实在创作新的科幻电影。她在花费额度作弊刷好感,和放任德子自己摸索出导弹间权衡片刻,还是选择前者,趴在场地中间一张桌子上细化起刚刚的火箭草图。
末了,她还补充:“其实现在做的火箭也能用,只是用途不同,如果您们想继续研究,我可以为您们联系……军械局的卡尔·贝克尔博士中校。”
这位中校是位弹道工程师,凯塞林的同事,她查过,这人后来设计了600毫米的卡尔臼炮,是“口径即正义”理论的坚定拥护者。
除了刷刷好感,早点发明导弹去炸鬼子也挺好吧?
她这样想着,又走向别的参赛小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