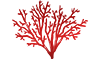下午五点,天色黯淡,又经过一阵激烈交火,叛军毫不意外地投降了。
海因里希·赫尔德被士兵从附近一处公寓的床上揪出来,衣衫不整地拖到广场上,跟其数百名个幸存的叛乱者站在一起。救援队开始给所有伤员包扎,驻军则用几辆大卡车精确地分拣着平民、驻军和救援队的尸体,叛乱者的尸体简单堆在一旁,等待验明正身。
广场上到处是掉落的弹壳和鲜红的血迹,腥味重得堪比屠宰场。陈澄被冯·勒布催促着前往广场去见海因里希·赫尔德,都得捂住口鼻,小心下脚。
按照这位少将的说法,现在才是“谈判”的时机。
“赫尔德先生,您为什么要发起叛乱?”
赫尔德摇头:“你要灭亡我们,还要问我为什么?”
“……”陈澄实在无语,上前一步愤怒地盯着对方:“我灭亡你们?难道我下令屠杀所有你们的党员?还是下令屠杀了天主教信徒?我给你们留了足够的退路,是你们要自取灭亡!”
“你在毁灭巴伐利亚人的独立思想!”
“我就是巴伐利亚人!我家就在慕尼黑!”陈澄掏出身份证件举到对方面前:“我知道怎样能让巴伐利亚变得更好,绝不是独立,绝不是从德国的庇护下离开,成为被各方觊觎的一块肥肉!”
“你是普鲁士人的狗!你从未把你自己当巴伐利亚人!”
对方固执地啐了一口。
陈澄知道这人说不通了,但围观的人群必须说通,否则这样的叛乱还会层出不穷。
“你分得很清,谁是巴伐利亚人谁是普鲁士人,谁是萨克森人谁是汉诺威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世界并不是一个巴伐利亚或是一个普鲁士就能主宰的,除了德国,欧洲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欧洲之外,还有美国、中国、还有很多国家。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且它并不和平,今天你不团结更多人,明天你就会被世界淘汰!”
“你只是花言巧语,要我们为普鲁士的战败赔钱罢了。”
冯·勒布伸腿踹了他一脚。陈澄赶紧去拦。
“赫尔德先生,什么叫普鲁士的战败?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是塞尔维亚人枪杀了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啊,按您的说法,奥匈帝国跟普鲁士人更亲近还是跟巴伐利亚人更亲近呢?”她仰起头直视对方:“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奥匈帝国跟谁更亲近?”
赫尔德定定地看了一会儿,别开眼睛。
令她没想到的是,冯·勒布冷笑了一声。
“战胜时享受红利,战败却不愿承担赔偿,你不配当巴伐利亚人。我出生在兰茨贝格,参加过世界大战,获得过马克斯-约瑟大骑士勋章,”他仰起头:“我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你那时在做什么?准备给军队‘背后一刀’吗?”
他挥手示意副官过来:“把法官找过来,现在就审,审完立刻枪决。”
“……”都要枪决了,审判有什么意义呢?
趁着对方还没开枪,陈澄赶紧问出她最关心的问题:“你是怎么凑出这么多人进军市政厅的?是党员,还是信徒?或是别的什么人?”
赫尔德没有说话。
陈澄长叹一声,转向冯·勒布:“将军辛苦了,接下来的工作由州政府接管吧。”
冯·勒布一言不发,立刻离开,把参谋长凯塞林留下来处理后续事务。
天黑后,作为巴伐利亚州文化处秘书的沃尔夫才姗姗来迟,小跑着进了已被层层看守和加班清理的市政厅里:“总理阁下,实在不好意思。叛乱发生时我不在慕尼黑境内,在班贝格,没有第一时间向您通报。”
陈澄没想到又一个傀儡掉链子,立刻把莱因哈特叫过来让两人对线。
“几千人的调动不是小动静,你们难道没发现?”
“他们之前只是游行,没有过激行为,加上马上要到狂欢节了……”
慕尼黑确实会在每年二月份的某个周二举行狂欢节。
陈澄皱眉:“那为什么救援队会有机枪?”
莱因哈特看了眼玛丽恩广场的方向,低声回答:“因为纳粹党的褐衫暴徒们简直不要命!他们甚至会使用土制炸弹袭击我们的巡逻小组和其他党派的集会人员!为了维持秩序,我们只能加大火力!”
“哪来的爆炸物?”
“硝化物本来就很好找!”他愤愤然:“这两年到处都在建高速公路,路不平的地方就要爆破,工地上很多炸药。”
陈澄几乎忘了这茬,顿感棘手。工程用炸药多普遍,总不能因为怕偷就不修路吧?
“炸药不要堆在工地上,用多少拿多少,多的用完就运走,使用期间由专人运输看管。”她记下这件事,又问:“去年底我回慕尼黑的时候,这里还好好的,这一个多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俩有谁能准确说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出了事情的大概。
去年11月,陈澄对各州政府高层进行小换血,巴伐利亚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被换下。当时除了小规模抗议,并没有什么异常,直到新年后才开始组织非正式游行抗议。因为游行主题除了推动巴州独立外,还增加了反普鲁士霸权和反犹太人,逐渐吸引了一部分纳粹冲锋队参加。不过前两天,冲锋队忽然集体脱离抗议队伍,新政府又因狂欢节临近而打算将他们强制驱离,这才引爆了冲突。
正好也因为狂欢节,新州长提前告知莱因哈特加派人手管理秩序,才能及时应对这场暴动,只是由于事出突然,加上召回休假状态的队员需要时间,为免事态失控,莱因哈特额外通知了巴伐利亚军区。
放莱因哈特和沃尔夫离开后半小时,陈澄又见到了海因里希·缪勒。
小个子的慕尼黑政治警察身板笔直,目光锐利,见面之后先行礼,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摊开来放在掌心,一副等候提问的乖学生模样。
陈澄没客气,直接问:“关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次暴动,你知道多少?”
缪勒也没让她失望,对着自己的笔记本娓娓道来。
表面上这是小党派对抗中央政策的一次血腥尝试,背地里还涉及到了宗教问题。
最开始被挪入观察团后,赫尔德就在参议院抗议过,但被中央党人私下劝住了,大概说了些为德国大局之类的话。等了一年,没等到对巴伐利亚人民党有利的消息,反而等到了赫尔德被撤职,柏林中央接管巴伐利亚。他们觉得受到欺骗,再次找到中央党人对峙。
这一回惊动了德国境内的几位主教们,慕尼黑大主教米夏埃尔·冯·法乌尔哈贝尔枢机紧急联系柏林大主教,四方人马在慕尼黑举行讨论会,聊了半天才意识到陈澄的宗教政策是“尊重”,这意味着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保持中立,却不意味着愿意与梵蒂冈保持友好关系,更不意味着会跟梵蒂冈一起反共。
巴伐利亚人民党和慕尼黑大主教希望陈澄能尊重巴伐利亚的自主自治权,中央党人表示他们曾在内阁会议上试探过她的立场,没有获得明确答案,加之彼时德国正在全力应对经济问题和扩军问题,找不到开口的机会,于是拖到了年后。
年后的形式更加不乐观。因为德法两国就驻军和赔款问题谈不拢,加上有小道消息称陈澄之所以在宗教中保持中立,是因为跟信仰天主教的父亲(鲁普雷希特)关系不好,进而厌恶整个宗教,党内部分成员认为自己同时被世俗政权、党派领导和宗教领袖抛弃,开始自发组织游行,吸引了部分纳粹党人。
希特勒得知消息后,紧急召回参加游行示威的纳粹党员,导致后者更加孤立无援。
赫尔德作为前巴伐利亚州长,半主动半胁迫的成了本次叛乱事件的主谋。叛乱的真正组织者声称这是一次“维特尔斯”式的威胁,目的是像陈澄叫嚣战争向法国施压一样,向陈澄极限施压以获得巴伐利亚的自主权。他说动了赫尔德默许他以赫尔德的名义召集党的成员参与本次叛乱,亲自带队冲击市政厅,直到被赶到的驻军击伤俘获。
“自1924年起我就一直关注着整个巴伐利亚的各个政治团体,积攒了不少资料,在来这里跟您汇报前,我已经见过这位组织者了,他中了3枪,活不过今晚,好在我及时拿到了他的口供。”
缪勒将记事本中夹着的两张纸递了过去,上面是满篇潦草的字符,结尾处有个鲜红的,透着血腥气的指印,盖住了一个断断续续的潦草签名。
陈澄没有接,她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一个两个都摸着她过河?一个无名NPC的主观能动性这么强吗?她忍不住想,要是她没搞集权,这老哥没被逼到绝路,再成长几年,是否有可能真带着巴伐利亚独立?
可惜世事没如果,他死了。
她知道德国的宗教问题一直很重要,但国内没有那么久那么深厚的宗教影响史,实在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她的态度是“尊重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宗教的自由,尊重公民信仰任何合法宗教的自由”,这只能算求稳,会让教廷有顾虑也是正常的。她不知道会这么严重,严重到这些人用生命来追求自主。
“希特勒是怎么解决宗教问题的?”
“宣称反犹反共,获得教皇的默许和支持,加强个人威信,代替宗教崇拜。”
“……跟宗教势力相比,纳粹思想也算进步吧?”
“你定义的‘进步’是什么。”
陈澄仔细思索片刻,决定放弃:“非要说的话,纳粹发动战争固然害死了几千万人,宗教对人的荼毒也不浅。现在只能庆幸让孩子们学生物学没有被教会强烈反对。”
“那是因为你没有下定论,你只是把各种学说可能性都列出来,然后以鼓励学生自行去探索真相为理由,让学生自发否认宗教的种种思想,这通常被叫作‘曲线救国’。”
“当一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信教,你不信教,你就是该被烧死的异端。”
还能怎么办呢?宗教势力可以徐徐图之,纳粹党却是来势汹汹。如果非要从暴毙和慢性死亡中选一个,她还是会选慢性死亡。何况巴伐利亚有超过80%的人口信天主教,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民意。
她忍不住叹息,拍了拍缪勒的肩膀以示倚重:“麻烦你了,请帮我约见这位冯·法乌尔哈贝尔枢机。”
希望大主教愿意出面稳定教徒们,平息动乱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