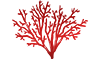二零二三年,立冬前三天。
陈风看了看时间,四点多了。
天阴的和黑天了似的,隔着车窗,只能看见一排光秃秃的绿化树,在大风里,配合着车内的音乐,有节奏的摇摆着。
才十一月,只打雷不下雨的刮着风,要下雪估计还得几天。
导航女声温柔道:“前方五百米,红绿灯路口,请直行。”
陈风低头瞄了一眼手机,这条路她来来回回走了快五六遍了,导航像是鬼打墙了,这最后五公里的路愣是走了快40分钟了。
不知道是这里路太复杂了还是太难走了,现在她有了点结论,估计是前者。
眼前这个见了一二三四五次面的红绿灯一如既往的保持非礼勿视的姿态,这种拒绝沟通的态度尤其让人火大,一瞬间她都想转头开回去了。
突然,手机弹了一条消息。
是周教授。
-到了吗?
-这次的项目我之前做过,刚才翻出来上次配合调研的孙女的联系方式,我已经和她们联系过了,倒时候有什么麻烦可以找她们帮忙。
随后,发过来了个好友分享。
名字很有个性,是西班牙语,叫Destreza。头像和名字一比逊色不少,是个露着肚皮的橘猫。
很酷的名字和很懒的猫。
陈风回了个比“ok”的表情包,发送了好友申请。
她看了眼熟悉的红绿灯,叹了口气,揉了揉酸痛的脖子。
算了,走吧大不了再来见你第一二三四五六次。
就在白色suv刚起步的时候,右边突然炸出一声引擎嘶吼。
一辆黑色摩托车斜刺里杀出,车头一翘,几乎贴着她的保险杠甩尾。泥水溅起半扇窗那么高,啪一声糊满挡风玻璃。
陈风一脚刹车闷死,整车ABS咔哒咔哒打颤。她被安全带猛的拉住,头撞在后座上,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看到了无数颗星星。
车玻璃被甩起来的泥水盖了一层,看不见那位不速之客,只听见她很冷的声音:“会不会开车?!瞎啊?!”
摩托骑手单脚点地,回头,黑色头盔镜片“嚓”地弹开——她烦闷地下了车,走到白车……啊不,现在变成了泥车,敲了敲前引擎盖。
陈风惊魂未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激起了脾气,推开车门,冷风瞬间灌入:“你直接插进来,还有理了?这是个路口看不见吗?!行车要按照交规行驶。”
“交规?”那人嗤笑,把头盔往上一推,露出一截被雨浸透的眉,尾锋像刀背,“这路口三天没灯了,没灯靠哪条交规,我给你打手势了没看见?把SUV当坦克。”
“行,你手势厉害,最好下次用手势拦闪电。”
“放心,闪电认得路。”那女人又把头盔前盖放了下来,“你呢?把导航当妈,妈一哑,你就断奶。”
陈风被噎得太阳穴直跳,抄起副驾的保温杯想摔,发现是导师送的“出师茶”,又原模原样放回。
那女人笑得牙尖,松离合,摩托像黑豹蹿出,车尾甩她一脸尾气。错身那瞬,陈风看见她摩托车后尾贴了一行白线:——
Needle & Thunder。
………
摩托车简直像为这小城的脉络量身打造的活物,在雨后的窄巷里游刃有余地穿梭。它最终一个利落的甩尾,钻进一条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被两侧高墙挤压得几乎看不见天的深巷。
巷口低矮的雨棚底下,已经蹲着、靠着、歪着三五个年轻人,烟头的红点在潮湿的昏暗里明明灭灭。雨水从棚沿滴答成串,在他们脚边溅开细小水花。
“悬姐!你再不来,我们可就打110报案,说你让富婆拐跑包养了!”一个剃着青皮寸头的年轻人率先起哄,咧嘴笑出一口白牙。
“包你大爷。”李悬利落地拔下钥匙,摩托车头一歪,毫不客气地横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中央。
她随手抄起靠在棚柱上、一瓶开了盖的冰镇啤酒,瓶身还挂着冷凝的水珠。她看也没看,仰头就灌下去大半瓶,喉结急促地滚动。
“刚来的路上,碰见一姑娘,犟得很,脖子以下全是规矩,吵了两句。”她甩甩头,水珠四溅,语气随意得像在说天气。
“哟嗬!新鲜!吵赢了吗悬姐?”寸头来劲了,往前凑了凑。
蹲他旁边、梳着夸张飞机头的男人用手肘不轻不重地怼了他一下,挤眉弄眼地笑骂:“废什么话!悬姐跟人吵架什么时候输过?没理都能搅出三分理,站着吵累了还能坐摩托上吵!”
“去你妈的!”棚底下爆出一阵哄笑,驱散了巷子里的阴湿气。
李悬也跟着嗤笑一声,抬手,空啤酒瓶划破空气,带着风声,“啪”一声脆响,精准地落进几步外的绿色大号垃圾桶里,声响在狭巷里回荡,像抽了一记漂亮的空鞭。
“别跟这儿屁叨叨没用的,今晚干正事。”
她弯腰,从摩托车坐垫下抽出一只看起来沉甸甸、饱经风霜的军绿色帆布包,啪地扔在雨棚下唯一一张干燥的小木桌上。
拉链一拉到底,露出里面码放得异常齐整的家什:一排排不同颜色的、标签密密麻麻的小药瓶,一次性无菌针帽封装在透明袋里,几支不同型号的纹绣笔,还有最扎眼的一—一台明显被暴力改装过的、银灰色袖珍热转印打印机。
它的打印头被整个拆掉,替换上的是一组闪着金属寒光的、可灵活拆卸的12针排线,紧密地排列着,看上去活像一挺微缩版的机关枪弹匣。
“老规矩,”李悬的手指在那排“弹匣”上滑过,语气不容置疑,“今晚必须给‘小柏林’后背那块收官。明天一早,那小子还指望靠着它去镇场子嘚瑟。”
“嘚瑟?”寸头有点没反应过来。
旁边一个一直默默抽烟、手腕上纹着般若的男人吐出口烟圈,哼笑一声接话:“嗯呢,就那小子,前两天不是找张枫纹了一双花臂么?嘚瑟得尾巴快翘上天了。小柏林啥脾气?他能咽下这口气?这不,砸了攒了半年的钱,求到悬姐这儿,要来个狠的,一步到位。”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悬姐仗义,接了。”
“悬姐仗义!”几个人跟着附和。
李悬没接这话,只是抬眼。
巷子穿堂风过,吹得雨棚边缘挂着的一串旧易拉罐和贝壳做的风铃胡乱碰撞,叮铃哐啷响成一片,吵得人心烦,像催命符。
她伸出还带着酒液湿气的手指,精准地拨弄了一下那串吵闹的风铃,声音奇异般地低哑下去。
“活儿给你干漂亮,但出去别满世界嚷嚷是我李悬的手笔。”
她目光扫过众人,带着点警告的意味,“我不想跟张枫打什么无聊擂台,没劲。”
她顿了顿,从帆布包侧袋摸出包烟,磕出一根叼上,旁边立刻有火递过来。
她凑近点燃,深吸一口,烟雾模糊了她侧脸的线条。
“另外,插个事。后街阿灿家那只蠢猫又他妈跑了。黑的,就尾尖有一小撮白毛,像蘸了墨。谁眼睛亮给找着了,”她吐出口烟,用夹着烟的手指点了点桌上那堆价值不菲的工具,“我免费给他纹一句,字随他挑,‘喵爷在此’也行,‘铲屎官跪安’也行,位置大小都随他。”
“收到!悬姐!”
……
陈风那边,导航终于重新上线,却毫不意外地提示她“已偏航,正在重新规划”。
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的感受,意料之中,不过还是很来气。
她低头一瞬,再抬头,前方堵成一条钢铁蜈蚣——红绿灯坏了,四条路的车互不相让,喇叭声把雨都震碎。她忽然想起那女人临走前的手势:左手食指中指并拢,往左一划,像给世界切出一条暗道。
“神经病。”她骂归骂,还是下意识打了左转灯,顺着那条暗道般的缝隙滑了出去。
陈风的目的地只有个大概到什么省什么市什么区,连街道都没有个大概范围。
绕来绕去,虽然出了导航的怪圈,可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心情不好,但也算不上烂,她是个自我内心调节很好的人,骂了一声神经,把刚才的郁闷和气愤一齐发泄出来了。
到点了,随便吃点什么吧。
不过刚才在路上转了这么久,也没找到一家看上去可以不中毒的店。
中毒是什么感觉啊?会看见什么吗?
应该不会,估计是口吐白沫,嘴唇发紫,躺地抽搐。
陈风甩了甩头,随便导航了个听说过的连锁酒店,能赶紧洗个澡躺下了休息最好,别管吃了。
酒店位置不错,楼下有几家认识的快餐品牌,至少温饱问题在这片得到了解决。
陈风后备箱放了不少的东西,整齐地码着密封袋、无酸纸、防潮箱等——一套田野考古的“行头”。
她看了眼这堆东西,只拎了行李箱出来:“拜拜。”
酒店前台办理入住很快,她看见床的一瞬间,简直想哭出来,把自己扔上去,好好舒展一下窝在车里的四肢。
不过,自制力还在,她拿出衣服就冲到浴室洗了个热乎乎的澡,舒服的她想高歌一曲。
水从上而下流着,不知道怎么的,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陈风努力地想看清这个小城市的样子,不过脑子里除了不怎么宽的单向道,就是哑火的红绿灯,还有……
那双眼睛陈风还记得,很圆,眼线拉的很长,看上去有点无辜。
不对,无辜的不是她,是自己。
她闭上眼睛。
很快又睁开。
下午周教授发来的大橘猫还没通过还有申请,那个头像也没了一开始感觉的可爱,反而多了点儿欠揍。
好像一直嘚瑟,说着:“你来打我噻,你来打我噻。”
陈风是第一次自己独自调研。以往,她总是作为学生或助手,跟在导师周教授身后,记录、整理、分析。
周教授像一棵大树,为她挡开了许多繁琐的事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她能专注于学术本身。
她回想起跟随周教授走过的许多地方,拜访过的无数手艺人。那些精美的技艺、悠久的传承、蕴含的文化密码,曾让她无比着迷。
他们记录下一卷卷访谈录音,拍摄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撰写了厚厚的研究报告,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项目结题时也总能获得不错的评价。
然而,陈风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疑问:然后呢?
报告被束之高阁,论文只在学术圈内流传,热热闹闹的“非遗日”活动过后,一切似乎又归于沉寂。宣传越来越多,标语越来越响,但那些真正支撑着这些技艺活态传承的土壤——市场的认可、大众的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接续力量——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她见过太多手艺精湛的老艺人,对着镜头笑容满面地展示技艺,转身却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徒弟而发愁,为作品销路不畅而叹息。
非遗,在很多情况下,似乎变成了一种被观赏、被研究、被保护,却唯独缺乏旺盛生命力的“标本”。
这种撕裂与挣扎,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关系,是那些格式化的调研报告和数据分析所能涵盖的吗?是几句“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口号所能解决的吗?
陈风走到窗边,看着雨幕中朦胧的青石巷。她忽然意识到,或许她过去所做的,更多是一种“记录”而非“传播”,是“研究”而非“连接”。
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它似乎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将深邃的文化知识隔绝在了象牙塔内,未能真正有效地转化为滋养传统技艺生存下去的活水。
她需要一种更直接、更富有情感、更能打破圈层壁垒的方式。
一个念头在她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她要做一档电台节目。
不是那种官方宣传式的播报,也不是深奥的学术讲座。她想要的,是一个能让人安静下来,用心去“听”的角落。
在那里,她会邀请用一辈子专注在一件事的剪纸手艺人,慢慢地讲述一张剪纸背后的故事、一个纹样的吉祥寓意、一把剪刀陪伴一生的岁月痕迹;她也会探寻“叛逆者”的想法,听他们诉说传统赋予的滋养与束缚,以及如何在冲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她要去记录那些技艺背后的心跳、温度、困惑与坚持。
这是陈风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或许比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更困难,也更“不务正业”,但她觉得,这或许才是她真正应该去尝试的方向。
她需要找到打动人心、连接彼此的声音。
她打开笔记本,看着第一页郑重地写下的《听见手艺》电台策划草案。
这是她的电台的第一站,万事开头难。